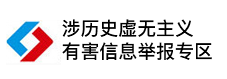王劭華
老付叫付仲新,是蔣家堰鎮碾盤溝村3組貧困戶。
初見老付,他的臉是陰著的。“臉不好看”,我心里嘀咕著。
但不好看也得看,我是老付一家的扶貧包保干部,至少三四年內,我時不時地就要接受這張臉的“考驗”。想到這兒,我打起十二分精神要與這個窮“親戚”拉近關系。可老付卻并不領情,他稍稍后仰著身子,蹺起二郎腿,目光在門頭、天花板和兩邊的墻壁上游走,有一句沒一句地搭理著我。
中午駐村工作隊的飯又夾生了,吃著堵心,我放下碗到院子里溜跶。
“你包保的是哪幾戶?”村干部過來搭話。
“付仲新......”我答到,“老付這個人好像不好打交道啊”。
“他這個人肯吃苦,能干,做活路沒得說的,就是有點倔。這幾年家里不順,脾氣更差了。我們和他打交道他從來沒給過好臉色,進他的門,想理理你一哈兒,不想理,你連水都喝不到一口。”村干部咧了下嘴,看來,他的飯也沒吃好。
老付日子本來過得還湊合。憑著他的吃苦能干,家里早早就蓋起了磚混結構的房子,兩個出嫁的女兒也孝順,隔三差五回娘家看望二老。兒子雖說初中畢業后沒上高中,但懂事,出門在北京打工幾年了,每年都能給老付寄點錢,盡管錢不多,顯然自己衣食能自保。
天有不測風云。2014年,老付的老伴中風了,老付辛辛苦苦攢下的積蓄被掏空不說,還欠下一屁股債。出院后,老伴落下半身不遂,還得天天吃藥,老付的日子愈發艱難起來。
老伴生病之前,老付在農閑時四處找活兒干、打短工,到手的是現票票。現在,老伴吃喝拉撒都得老付照顧,用老付自己的話說,他是“哪兒都去不了,啥也干不成,地里的莊稼都荒了,更別提打短工了,看著錢掙不著”。
隔年,低保政策口徑變了,接著就是大清理,老付家的低保被清理掉了。從此,在老付眼里,天都是黑的,看哪兒都不順眼。
第二次到老付家,老付的老伴正坐在靠近門口的椅子上曬太陽,我和她聊了起來。老付的老伴是個急性子,提到過年沒回家的兒子,老伴破口就罵兒子不孝。我安慰著,然后掏出手機,向老付要了兒子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,在和老付兒子通話時,老付直勾勾的盯著我的手機。了解了老付兒子打工的情況后,我把電話向老付遞過去:“不和兒子說幾句?”老付稍稍一愣,緊接著就把手伸了過來。看得出來,老付有日子沒和兒子聯系了,他在和兒子說話時,沒有像老伴一樣的埋怨,眼中有一抹柔光閃動。
掛斷電話,遞給我,老付沒有說謝謝,但臉色舒緩了很多。
因為照顧老伴離不開身,老付只能就近謀收入。除了向老付建議多養豬和雞之外,我找到村干部,把村里養護村道、巡護山林的活兒交給了老付。老付的老伴己經享受了新農合慢性病定補,考慮到老付的實際困難,我替老付向民政提交了臨時救助申請,同時,也遞交了低保申請。農忙的時候,我就和老付一起到地里收玉米......
日子一天一天過,老付的臉一天一天舒緩起來。
轉眼到年底,縣里的考核來了,老付住在村尾村道旁,被抽中接受入戶調查的概率高。盡管這一年里,老付喂了3頭豬、50只雞,收了2000斤玉米,領到1600元臨時救助金,除了在村里干活掙的工錢,還拿到4700元獎補。低保的事辦的差不多了,轉過年,就能享受待遇。但老付究竟是張什么臉,我心里還是在打著鼓。
又是一次包保干部集體進村入戶。中午飯后,大家紛紛說起這次鎮里考核的情況。提到老付,村干部竟有點激動:“老付跟變了一個人樣的,這次鎮里考核,他不僅對幫扶情況說的清清楚楚,還笑呵呵的,熱情的很,這多年,我還是頭一回看到他對干部有笑臉....”
“今兒的飯煮的還好吧”,我問村干部。
村干部:“好!今天的飯正合適,呵呵。”